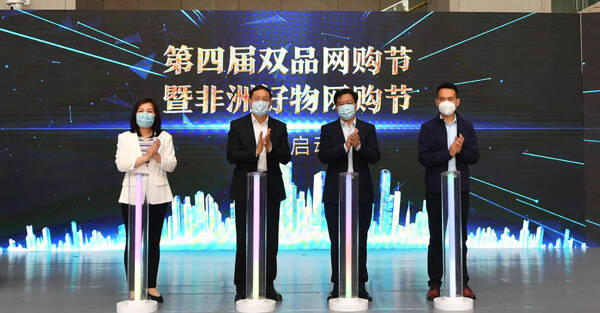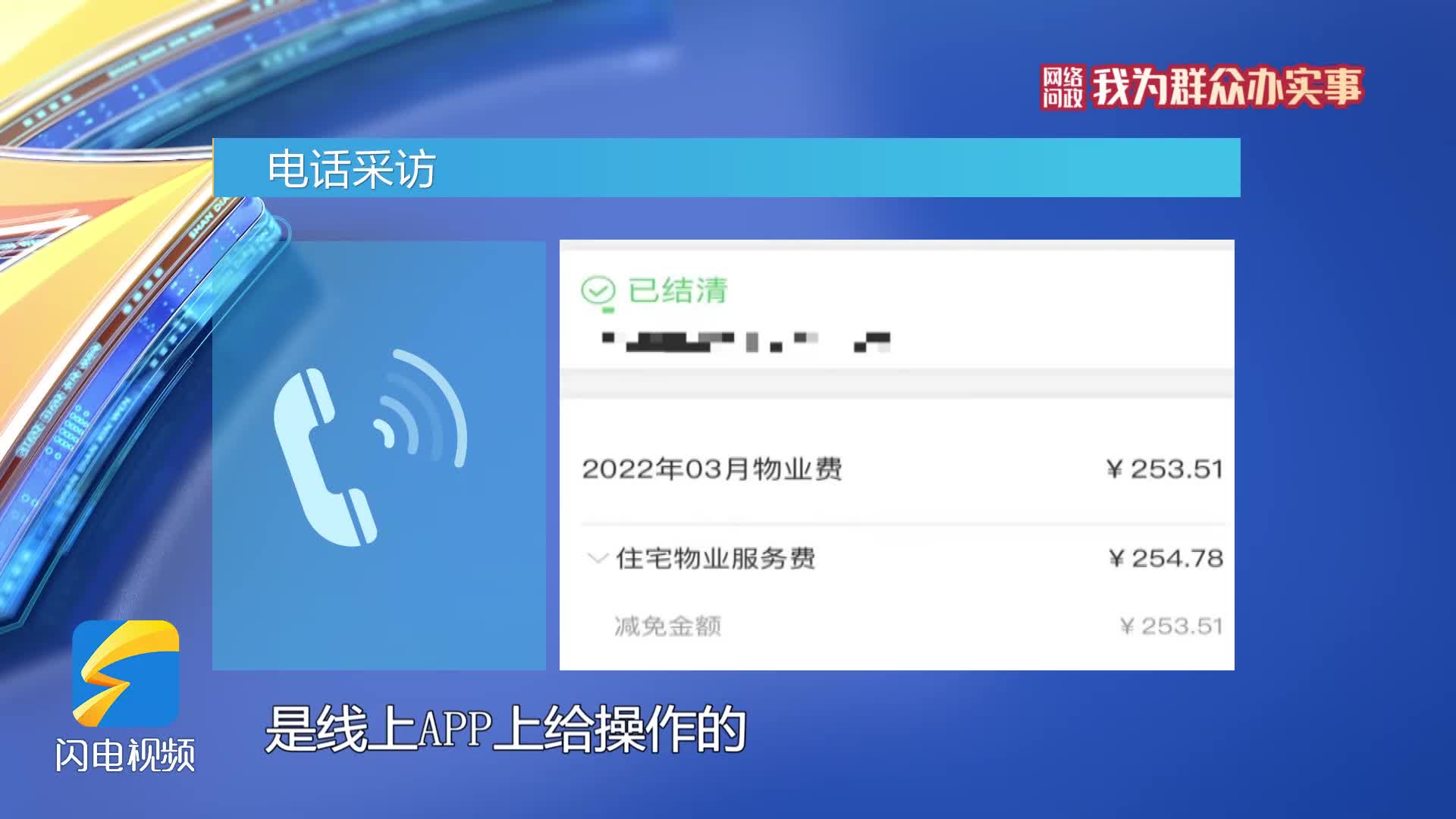濟(jì)南75歲老人開(kāi)了家庭博物館,14000多件老物件里的人世間
來(lái)源:海報(bào)新聞客戶(hù)端
2022-05-18 15:22:05
原標(biāo)題:濟(jì)南75歲老人開(kāi)了家庭博物館,14000多件老物件里的人世間
來(lái)源:大眾報(bào)業(yè)·齊魯壹點(diǎn)
記者 李靜 張錫坤
崔兆森的家庭博物館,開(kāi)在濟(jì)南恬靜又市井處。
這家博物館像一個(gè)磁場(chǎng),匯聚著14000多件生活中的老物件,和崔兆森一家三代人的“人世間”。而這個(gè)磁場(chǎng),輻射出一個(gè)普通家庭70年的命運(yùn),又悄無(wú)聲息地回答了家庭、社會(huì)與時(shí)代如何相融的問(wèn)題。
在5月18日國(guó)際博物館日來(lái)臨時(shí),記者來(lái)到崔兆森的家庭博物館,看看一個(gè)家庭博物館的故事,和這家博物館的力量。
崔兆森帶記者參觀博物館
地下室藏著一家博物館
在濟(jì)南經(jīng)七路春元里小區(qū)的一處地下室,藏著一家“齊泉博物館”。
所謂“齊泉博物館”,意指“齊魯泉城”。博物館的主人是今年75歲的崔兆森,一個(gè)地地道道的老濟(jì)南人。在400平米的博物館里,崔兆森收藏了14505個(gè)老物件。
這些老物件不是價(jià)值連城的奇珍異寶,而是崔兆森一家三代人生活中用過(guò)的老物件。小到糖紙、信件、鉛筆,大到縫紉機(jī)、電視機(jī)、自行車(chē)……處處都是歲月的味道。
崔兆森將收藏的《大眾電影》雜志做成“封面墻”
關(guān)于崔兆森辦這樣一個(gè)家庭博物館的初衷,要從1994年講起。那一年,崔兆森妻子的單位分了一套三居室的宿舍。崔兆森說(shuō),“兩間做臥室,一間當(dāng)書(shū)房,我決定系統(tǒng)地整理一下以往的生活資料。”
崔兆森,1966年高中畢業(yè)。1970年,崔兆森入伍到部隊(duì)當(dāng)兵,曾經(jīng)多次受過(guò)嘉獎(jiǎng),并立過(guò)三等功。當(dāng)了15年兵,崔兆森從部隊(duì)退役到機(jī)關(guān)單位工作。
在部隊(duì)時(shí),崔兆森曾擔(dān)任文化干事,分管電影組,經(jīng)常下連隊(duì)放電影。崔兆森對(duì)《大眾電影》雜志情有獨(dú)鐘,“當(dāng)時(shí)能看電影,看報(bào)紙,就是我們?nèi)康臉I(yè)余文化生活。而電影,對(duì)我們這代人有著舉足輕重的作用。”
為了淘換一本《大眾電影》雜志,崔兆森跑過(guò)很多城市。“那時(shí)候網(wǎng)絡(luò)不發(fā)達(dá),收藏不像現(xiàn)在這么方便。”崔兆森常常坐火車(chē)到上海、南京等城市,輾轉(zhuǎn)多個(gè)文化市場(chǎng)、舊書(shū)市場(chǎng),一本一本地淘《大眾電影》雜志。
2002年,朋友告訴崔兆森在濟(jì)南一個(gè)文化市場(chǎng)有一本《大眾電影》創(chuàng)刊號(hào)。崔兆森騎上車(chē)就到文化市場(chǎng),花了2800元錢(qián)買(mǎi)下這本創(chuàng)刊號(hào)。2800元,對(duì)于他來(lái)說(shuō)不是小數(shù)目,但是經(jīng)驗(yàn)告訴他,一旦遲疑就會(huì)錯(cuò)失這本雜志。崔兆森說(shuō):“之前有一篇寫(xiě)我的文章,叫《尋尋覓覓十年路,一步之遙大團(tuán)圓》。一直到我買(mǎi)下這本創(chuàng)刊號(hào),才真正實(shí)現(xiàn)‘大團(tuán)圓’了。”
《大眾電影》雜志成為崔兆森漫漫收藏路的開(kāi)端。經(jīng)過(guò)20年的積累,崔兆森的收藏達(dá)到了一定的規(guī)模。2015年9月25日,崔兆森創(chuàng)立了“齊泉博物館”。
14000多個(gè)老物件里的舊時(shí)光
在崔兆森的齊泉博物館里,舊時(shí)光“看得見(jiàn)”“摸得著”。
循著時(shí)光的軌跡,博物館里年齡最大的老物件,要數(shù)上世紀(jì)二三十年代崔兆森母親曾經(jīng)穿過(guò)的衣服、父親用過(guò)的書(shū)本。
崔兆森的日記本
齊泉博物館的鎮(zhèn)館之寶,是崔兆森用50多年寫(xiě)的129本日記。“這些日記里,傾注了我最多的心血。”崔兆森說(shuō)。
“參軍入伍后,我憧憬著每一天的生活都是美好的。所以我就開(kāi)始寫(xiě)日記,一直堅(jiān)持到現(xiàn)在。”如今,這些日記本摞起來(lái)有兩米多高。崔兆森的日記很有特點(diǎn),就是將每一天的生活如同“流水賬”一樣記錄下來(lái)。
“1970年12月22日,早上穿上了一身軍裝,披掛了帽徽和領(lǐng)章。父母父母、妹及李榮送我出門(mén)。……到了部隊(duì),他們分別給我進(jìn)行了入伍教育談話。”這是崔兆森寫(xiě)下的第一篇日記。
“很多時(shí)候生活雖然單調(diào),但是現(xiàn)在再回頭看反而覺(jué)得很有意思。”崔兆森講到。
現(xiàn)在,崔兆森每天早上到齊泉博物館的第一件事,就是把頭一天的生活寫(xiě)在日記本上。
崔兆森還用自己“二指禪”的技術(shù),將這些日記陸續(xù)錄入到電腦里,總計(jì)1500多萬(wàn)字。“把日記錄入電腦以后,最大的好處就是檢索方便。”有時(shí),崔兆森偶爾想不起一件事情,就從電腦上檢索出來(lái)。
崔兆森說(shuō):“這些日記,實(shí)際上也是社會(huì)發(fā)展的大數(shù)據(jù)。我有很大的感受是,這一代人很難理解上一代人的生活。我希望后來(lái)人知道我們這一生是怎樣度過(guò)的。”
關(guān)于孩子的物件,崔兆森擺放得別有新意。一個(gè)嬰兒車(chē),裝有一臺(tái)電腦。“這兩樣物件,正是我們的孩子從出生到長(zhǎng)大成人的標(biāo)志。”
每年3000多人來(lái)館內(nèi)參觀
齊泉博物館每年會(huì)迎來(lái)3000多人,人們來(lái)尋覓記憶,或者存放記憶。
自從建起博物館,崔兆森便向公眾免費(fèi)開(kāi)放。每年寒暑假會(huì)有很多學(xué)生,來(lái)到齊泉博物館參觀。附近的社區(qū)和單位也會(huì)把黨建活動(dòng)安排到這里。齊泉博物館被評(píng)為“優(yōu)秀傳統(tǒng)文化傳承基地”“中小學(xué)社會(huì)實(shí)踐教育基地”。
來(lái)人參觀時(shí),崔兆森就會(huì)變成講解員,為來(lái)者講述這些老物件背后的故事。
很多人說(shuō),“我們家也有這些老物件,但是都沒(méi)有完整地存下來(lái)。到這里一看,感覺(jué)似曾相識(shí),會(huì)想起自己過(guò)去家庭的生活。”
陸繼琨捐贈(zèng)給博物館的音響
陸繼琨是眾多來(lái)訪者中其中之一。在參觀完博物館后,陸繼琨受到極大的觸動(dòng)。第二天,他又來(lái)到博物館,并帶來(lái)一大堆老物件捐贈(zèng)給博物館,其中有一臺(tái)音響和一本護(hù)照。
陸繼琨向崔兆森講起音響和護(hù)照的來(lái)歷。當(dāng)年,陸繼琨買(mǎi)這臺(tái)音響花了一萬(wàn)多元錢(qián)。“老陸一直注重追求文化生活。”崔兆森將陸繼琨的音響擺在他曾經(jīng)用過(guò)的音響旁,并標(biāo)注“人民對(duì)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們的奮斗目標(biāo)。”
陸繼琨的護(hù)照也很特殊。“老陸退休以后,去過(guò)85個(gè)國(guó)家,護(hù)照上蓋著85個(gè)章,最后章都蓋不下了。”崔兆森的博物館里放著一張?zhí)厥獾闹袊?guó)地圖。在地圖上,崔兆森在每個(gè)省份都附上了自己的留影。崔兆森說(shuō),“這些都反映著我們這一代人的生活。”
后來(lái),陸繼琨還將自己的自行車(chē)、旅行包等,都捐贈(zèng)到了齊泉博物館。崔兆森說(shuō):“大家很多老物件丟之可惜,放著沒(méi)用,就送到我這里了。”
崔兆森特地留出幾個(gè)柜子,為大家存放老物件,存放記憶。
“這是我們的人世間”
齊泉博物館里這些曾經(jīng)司空見(jiàn)慣的老物件,在一波一波時(shí)代浪潮退去之后,留存下時(shí)代的痕跡。
在一個(gè)又一個(gè)老物件前,崔兆森講述著科技的飛速進(jìn)步。“有了打火機(jī),火柴被淘汰了。有了計(jì)算機(jī),算盤(pán)被淘汰了。”
崔兆森還保存著老家“小緯六路南街”的門(mén)牌,“過(guò)去的很多場(chǎng)景在我們現(xiàn)在的城市里已經(jīng)遺失,但是從這些老物件里還能回憶老濟(jì)南的生活。”
平時(shí),崔兆森和哥哥一起打理齊泉博物館。“我75歲,哥哥81歲。現(xiàn)在每天打掃這里,我們感覺(jué)有點(diǎn)力不從心。”崔兆森說(shuō),“我想找到一家文化單位合作,幫我管理博物館,把這些歷史傳承下去。不過(guò)做這件事情,需要有情懷。”
崔兆森的家庭照
在齊泉博物館里,有一個(gè)獨(dú)特的相框。中間放了電視劇《人世間》的劇照,四周放著崔兆森一家人的照片。最近,電視連續(xù)劇《人世間》熱播,崔兆森也迷上了。崔兆森說(shuō):“我覺(jué)得《人世間》這部電視劇就是反映的我們這一代普通老百姓的人生。我這個(gè)小博物館,也是普通老百姓的生活切面。在這里,大家或多或少能夠看到自己生活的影子。”
崔兆森感慨,“我們父母那一代,生活不容易,艱苦奮斗了一生。我們這一代生活在一個(gè)和平環(huán)境中,經(jīng)歷了很多巨大變化。孩子們趕上了好時(shí)候,可以盡情馳騁在更廣闊的天地。可以說(shuō),我們與祖國(guó)同成長(zhǎng),共命運(yùn)。”時(shí)代,在每一個(gè)人身上都有具體的體現(xiàn)。
崔兆森寫(xiě)了一本書(shū),書(shū)名叫《家庭博物館里的中國(guó)——我家七十年》,里面詳細(xì)講述了家庭博物館里老物件的故事。山東大學(xué)《文史哲》主編王學(xué)典教授為崔兆森作序,“他以他的用心與堅(jiān)持,通過(guò)個(gè)人記述、個(gè)人檔案、個(gè)人收藏,對(duì)逝去的歷史實(shí)施了搶救,為時(shí)代變遷留下了一份生動(dòng)的記錄,留下了宏大歷史的私人‘切面’,這是十分難得的。”
采訪最后,崔兆森語(yǔ)重心長(zhǎng),“這是我們的人世間,希望大家看完博物館,能夠看清我們走過(guò)的路。”
想爆料?請(qǐng)登錄《陽(yáng)光連線》( https://minsheng.iqilu.com/)、撥打新聞熱線0531-66661234或96678,或登錄齊魯網(wǎng)官方微博(@齊魯網(wǎng))提供新聞線索。齊魯網(wǎng)廣告熱線0531-81695052,誠(chéng)邀合作伙伴。
走近封閉式管理下的臨沂凱旋醫(yī)療養(yǎng)老服務(wù)機(jī)構(gòu)
- 面對(duì)當(dāng)前疫情防控形勢(shì),按照省市區(qū)各級(jí)民政局部署,自3月12日起,臨沂凱旋各醫(yī)療養(yǎng)老服務(wù)機(jī)構(gòu)實(shí)施封閉式管理,切實(shí)保障老年人生命安全。近...[詳細(xì)]
- 在臨沂客戶(hù)端 2022-05-18
5分鐘,法律文書(shū)從山東到廣西
- “您好,山東省慶云縣人民檢察院向您發(fā)送法律文書(shū)一份,請(qǐng)盡快登錄微信小程序或關(guān)注慶云縣人民檢察院官方公眾號(hào)確認(rèn)接收。”近日,家住廣西...[詳細(xì)]
- 山東法制報(bào) 2022-05-18
煙臺(tái)牟平稅務(wù):政策直播送春風(fēng) 惠企利民助發(fā)展
- “尊敬的各位納稅人大家下午好,感謝大家百忙之中抽空收看我們的網(wǎng)絡(luò)直播課。本期直播課我給大家?guī)?lái)的是“我為納稅人繳費(fèi)人辦實(shí)事暨便民辦...[詳細(xì)]
- 濟(jì)南頭條客戶(hù)端 2022-05-18
煙臺(tái)稅務(wù):“一把手”走流程 走出服務(wù)新成效
- 近日,按照“便民辦稅春風(fēng)行動(dòng)”統(tǒng)一安排,煙臺(tái)稅務(wù)部門(mén)啟動(dòng)“一把手走流程”暨“當(dāng)一天納稅人”活動(dòng),市縣兩級(jí)稅務(wù)部門(mén)“一把手”通過(guò)到辦...[詳細(xì)]
- 濟(jì)南頭條客戶(hù)端 2022-05-18
山東能源集團(tuán)西北礦業(yè)揭牌成立
- 5月17日上午,山東能源集團(tuán)西北礦業(yè)有限公司成立大會(huì)在陜西省西安市召開(kāi),標(biāo)志著山東能源集團(tuán)整合優(yōu)勢(shì)資源,推進(jìn)西部開(kāi)發(fā)建設(shè)形成新格局。...[詳細(xì)]
- 大眾日?qǐng)?bào)客戶(hù)端 2022-05-18
山東能源新礦集團(tuán)協(xié)莊煤礦:開(kāi)門(mén)納諫聽(tīng)民意 卸下“包袱”變“財(cái)富”
- 山東能源新礦集團(tuán)協(xié)莊煤礦始終把職工的利益放在第一位,用心用情傾聽(tīng)職工心聲,暢通職工意見(jiàn)箱、“領(lǐng)導(dǎo)接待日”、職工維權(quán)站、職工代表座談...[詳細(xì)]
- 大眾日?qǐng)?bào)客戶(hù)端 2022-05-18
4月份房地產(chǎn)數(shù)據(jù)出爐!山東4市二手房較上月均下跌
- 5月18日上午,國(guó)家統(tǒng)計(jì)局發(fā)布2022年4月全國(guó)70個(gè)大中城市商品住宅銷(xiāo)售價(jià)格變動(dòng)情況。70個(gè)大中城市中,商品住宅銷(xiāo)售價(jià)格下降城市個(gè)數(shù)增加,一...[詳細(xì)]
- 中國(guó)山東網(wǎng) 2022-05-18
“2022年濟(jì)南消費(fèi)季”今日正式啟幕
- 疫情陰霾正散去,不少市民早已期待自在地買(mǎi)買(mǎi)買(mǎi)、逛逛逛,“2022年濟(jì)南消費(fèi)季”適時(shí)登場(chǎng)。5月17日,濟(jì)南市委市政府召開(kāi)新聞發(fā)布會(huì),介紹“2...[詳細(xì)]
- 濟(jì)南時(shí)報(bào) 2022-05-18
濟(jì)南12所高中招收739名推薦生筆試面試時(shí)間為5月22日、23日
- 5月17日,濟(jì)南12所進(jìn)行推薦生招生試點(diǎn)的高中相繼發(fā)布2022年推薦生招生工作方案,共計(jì)招收739名,2021年共招收723名。符合推薦生報(bào)名條件的...[詳細(xì)]
- 濟(jì)南時(shí)報(bào) 2022-05-18
濟(jì)南將全面推進(jìn)“十大之城”建設(shè)
- 建設(shè)信仰堅(jiān)定的紅色之城建設(shè)底蘊(yùn)深厚的文化之城建設(shè)聞名中外的天下泉城建設(shè)美美與共的溫暖之城建設(shè)品牌薈萃的魅力之城建設(shè)創(chuàng)新創(chuàng)意的活力之...[詳細(xì)]
- 濟(jì)南時(shí)報(bào) 2022-05-18
濟(jì)南市圖書(shū)館全面恢復(fù)開(kāi)放
- 5月17日,濟(jì)南市圖書(shū)館全面恢復(fù)開(kāi)放,開(kāi)放時(shí)間為9:00-17:30,逢周一閉館。中午12點(diǎn),在圖書(shū)館二樓區(qū)域,市民前來(lái)借閱圖書(shū)。濟(jì)南時(shí)報(bào)·新黃...[詳細(xì)]
- 濟(jì)南時(shí)報(bào) 2022-05-18
今年濟(jì)南12所高中招收739名推薦生
- 5月17日,濟(jì)南12所進(jìn)行推薦生招生試點(diǎn)的高中相繼發(fā)布2022年推薦生招生工作方案,共計(jì)招收739名,2021年共招收723名。符合推薦生報(bào)名條件的...[詳細(xì)]
- 濟(jì)南時(shí)報(bào) 2022-05-18
2021年濟(jì)南市發(fā)明專(zhuān)利授權(quán)量8208件,同比增長(zhǎng)40.7%
- 5月17日,濟(jì)南市委市政府召開(kāi)新聞發(fā)布會(huì),介紹全市知識(shí)產(chǎn)權(quán)運(yùn)營(yíng)服務(wù)體系建設(shè)和知識(shí)產(chǎn)權(quán)保護(hù)工作情況,新黃河記者從發(fā)布會(huì)上了解到,2021年...[詳細(xì)]
- 濟(jì)南時(shí)報(bào) 2022-05-18
- 立案7200余起 挽回和避免直接經(jīng)濟(jì)損失數(shù)百億元 山東公安重拳嚴(yán)打經(jīng)濟(jì)犯罪
- 你的笑容如此美麗!濟(jì)南初高中學(xué)子陸續(xù)重返校園
- 周乃翔到濟(jì)南新舊動(dòng)能轉(zhuǎn)換起步區(qū)調(diào)研
- 奮進(jìn)吧,山東|這五年,我們變了......
- 省委機(jī)構(gòu)編制委員會(huì)召開(kāi)會(huì)議 聚焦重大發(fā)展戰(zhàn)略加強(qiáng)前瞻性體制研究 為新時(shí)代社會(huì)主義現(xiàn)代化強(qiáng)省建設(shè)提供堅(jiān)實(shí)保障
- 1濟(jì)南新增本土確診病例6例無(wú)癥狀感染者37例
- 2力度+溫度 濟(jì)南強(qiáng)化重點(diǎn)公共場(chǎng)所疫情防控監(jiān)督檢查
- 34月18日濟(jì)南新增本土確診病例1例、本土無(wú)癥狀感染者14例
- 4山東籍孫紹騁履新內(nèi)蒙古自治區(qū)黨委書(shū)記,曾任山東省副省長(zhǎng)
- 55月起,青島這些人免費(fèi)核酸檢測(cè)地點(diǎn)、時(shí)間調(diào)整
- 62021年30省人口數(shù)據(jù)公布山東出生人口75.04萬(wàn)人
- 7利好!青島地鐵2號(hào)線東延段8個(gè)地鐵站點(diǎn)全線開(kāi)工!